【前言】2025年春季征兵工作开始启动。今天,分享校友胡国桥近期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署名文章《跨越战争与和平》。胡国桥1980年考入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1984年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戎马40年,从菁菁校园到绿色军营,从南疆战场到北国边关,一直在战斗,一直在坚守,一直在超越,热血男儿的青春在拼搏奋斗中闪闪发光。

跨越战争与和平
胡国桥
2022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作为解放军英模团代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当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我的眼里满是泪水,脑海中浮现着那些为了新中国,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英雄和一个个年轻战友的身影。近40年的军旅人生,也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我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一个国营农场里,辽阔的草原哺育了我,宽广的黑土地给了我奋进的力量。我从小崇拜军人,崇尚英雄,立志做一个国防建设的雄鹰,守护国土的安宁。
1980年我考入内蒙古林学院,在大学期间我担任学院学生会主席,多次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很少,在许多人的眼里,大学毕业生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我在大学毕业之即,却选择了投笔从戎报名参军,进入石家庄陆军学校,学习步兵指挥。
也许有人会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平静安逸的工作和生活而献身军旅?我是这样回答:“榜样的力量引导我,男儿报国无上荣光”
我上大学时,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还在持续进行,全国上下都在学习“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再见吧妈妈》《血染的风采》歌声唱遍大江南北,也激荡着我的内心世界,卫国戍边立功疆场的决心也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自卫还击作战英模人物的事迹让我热泪盈眶,使我们这些被誉为“时代娇子”的大学生热血沸腾。在举国上下“讲英雄、学英雄、做英雄”的氛围中,我参军入伍的决心更加坚定。
到军校后,第一件高兴的事就是穿上新军装,当时是56式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晚上睡觉时,我都把军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枕边,半夜有时还要抚摸一下。
但很快,新鲜劲儿就过去了,严格紧张艰苦的军校生活让我们面临着许多考验。一是伙食差。常吃玉米面大饼子、“钢丝面”(这是一种用烫的半熟的玉米面,通过轧面机挤出的面条,颜色金黄,怎么也煮不烂)。每顿饭全班20个人共4盘菜1个汤,少见肉荤。二是训练苦。早上五点半起床,摸黑穿衣服,3分钟在门口集合完毕,每天10多个小时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一环扣一环。凡事都要请假,上厕所也得先向班长报告。每周休息一天,外出(离开军营)按人数比例,一个月也轮不上一回。一遍遍搞卫生,叠被子、毛巾都要四面见线整齐划一,像四方豆腐块。枯燥辛苦的部队生活,我也曾产生了质疑,在这里能够实现理想吗?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磨练,强化了我的自律能力,也激发了我内心的潜能。开弓没有回头箭,别人能行,我也行!“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我暗暗下定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中,投入到火热的充满激情的军校生活中。
1985年6月,在我们即将军校毕业时,学校接到了总部关于选派部分学员去云南老山前线代职见习的命令。我内心澎湃,实现理想的机会来了。那天晚上,孙大淮教导员在大教室做参战动员,他一边讲,我一边写参战申请书,他刚讲完,我就第一个把请战书交上去。主要写了四条理由:第一,我是全中队唯一的正式党员,政治条件高;第二,我是全优学员,军事技术过硬;第三,登山比赛我曾获第一,身体棒;第四,我家兄弟4个,无后顾之忧。后来我又加了一条“我会蒙古式摔跤”。
我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那一年,军校从20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了56名学员,组成了北京军区赴滇参战见习连。出征前,我们把当时部队装备的54式手枪、56式半自动冲锋枪、班用轻机枪、40火箭筒、82无后坐力炮等武器打了个遍。
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全体毕业学员发言:“到边疆去,到前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请党和人民等待我们胜利的好消息!”
打仗就有牺牲,一个人要上前线打仗对家庭来讲,是一件大事。父母知道我的选择后,给我拍来了电报,上面写道:“愿儿英勇杀敌凯旋归。”父母的支持令我十分感动,给我增添了巨大力量。出征前,我的女朋友千里迢迢从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赶到石家庄,还带来了结婚介绍信,要“以妻子的身份”送我上战场。我对她深情地说:“相信我,等我戴着军功章回来”。
其实,这也是在激励我自己。她此时不知道,我和许多同学已写好了“遗书”,还对着录音机留下了“遗言”。
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她在车站送我时,追着火车向我招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85年8月16日,这是让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北京军区赴云南参战见习连在各级领导和石家庄市人民及亲友的欢送下,登上了由北京直达昆明的T61次特快列车,一路南下。
我们到达昆明后,转乘坐军用汽车进行摩托化运输,在盘山路上走了3天,沿途经过了多处少数民族村寨,路边有许多大人、小孩欢迎我们,他们还往我们车上扔水果和鸡蛋等。
1985年8月22日,我们到达麻栗坡县,驻在一个叫水地房的小村子里,那里条件很差,连电都没有。村民用柴草烧饭取暖,泥坯房熏得像煤窑一样黑。
在那里我们进行了10多天的临战训练,了解到当时敌我双方的作战焦点是在老山战区的那拉方向。而且,已经进行了1个多月的残酷战斗,我们所在部队414团1营3连增援到那里,坚守的166高地是战区的最前沿,高地三面受敌,距敌最近处只有七八米远,那里环境恶劣,战斗频繁,伤亡很大,急需补充战斗力量。
刚开始部队只分给我们见习排长一个名额去166高地,我立刻找到见习连带队的王东连长对他说:“听说去166只有一个见习排长名额,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是这批参战大学生中唯一的正式党员,这个名额说啥也是我的”。我的“后门”走通了。
当时的那拉口是整个老山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犹如锅底,被盘踞在居高临下的小青山、八里河东山方向的敌人监视着,我们在阵地上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敌人象恶魔一样,虎视眈眈地时刻盯着我们。
坚守在在这片阵地上的原67军199师595团,从5月19日接防后,先后取得了“5.31”“7.19”等较大规模战斗的胜利,打退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几百名战友在这里流血,有的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几个月的鏖战,这里的树木早已变成残肢和焦炭,绿色植被荡然无存,高地已经成了白花花的“采石场”,有的地方抓把土石里边都有几块弹片。在那拉口每天都有伤亡,这片阵地号称是“绞肉场”“人间地狱”。
在阵地左边,是日夜奔腾的盘龙江。河堤边上有一条公路,是两国交流的重要通道,如今这里成为敌人进攻的重要依托。这个交通要道一旦失守,敌人就可以畅通地向我境内发展进攻。所以,低矮的那拉口地区成为当时敌我双方相争之地。
1985年9月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们从临战训练地坐上汽车,向战区最前沿的那拉口方向开进。
枪炮声越来越近,有时敌人的炮弹落在公路旁的盘龙江里,炸起冲天水柱。车子开得很快,我们谁都不说话,车上十几个人手拉着手,似乎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汽车开到天保农场的船头(地名)就不能再往前开了,那里所有民房都被敌人的炮火摧毁,留下残壁断墙,战争气味十足,连厕所的窗台上都摆放着手榴弹!
在天宝农场的原来场部,我们吃了上阵地前的最后一次饭,算是“壮行餐”。没有茅台、红花和大鱼大肉,只是茄子、土豆和大米饭,我连吃了3大碗米饭。当时,我怎么往苦处想,也想不到,从那时起,在阵地上的77天里,我们每天只能喝雨水、吃压缩饼干与罐头度日。
我们把从军校带来的军装、被子、书籍和日用品全部放到这里,领路的军工(负责补给的参战人员)告诉我们,上阵地多带点裤头、背心和药品就行了,多了带不上去,也没啥用处。但是,我们向阵地机动时,让我给连里带上1部861电台。
我们在炮声中拉大距离,开始向阵地紧张地跑步前进。通往前沿高地的路,只有一条既流水又走人的堑壕,我们通过阵地边的战壕到一段沼泽地时,带路的战友告诉我们,前面是“百米生死线”,这里全部暴露在敌人的射程范围内。有的沼泽地水面上间隔铺着装子弹或炮弹的木盒,运送军需品和伤员以及部队增员,这里是必经之路。
通路坡陡泥滑非常难走,不时遇到暴露地段,还要快速通过,一路上不停地摔跤。摔跤也得有“规矩”,如果你往沟边上摔,那八成就死定了,因为除去沟中那条小路,其他地方全是雷区!
我们逐个飞奔穿过“百米生死线”的沼泽地,耳边的风呼呼的响,多想此时能长出翅膀。在路上躲过几次敌人的炮弹和冷枪袭击,终于到达了3连部所在的168高地。
这里有个山洞,是连指挥所也是一个战地医疗救护所。此时,天已黑,指导员姚庆和点上一个小蜡烛,挨个儿把我们照了一遍,算是认识了。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政工干部,是3连的核心。在夜幕的掩护下,利用敌人炮火的间隙,指导员催促我们快速赶紧上166高地哨位。
既然上了战场,就要视死如归的准备。我们振作精神,在带路战士的后面,依次出洞。在洞口,一个战士打开一箱手榴弹,发给我们每人一枚。我一看是77式木柄手榴弹。这比在军校时训练用过的67式手榴弹性能好,体积小、重量轻、威力大。可只有一个太少了吧,我想再要几枚,发弹的战士小声对我说:“多了不好带,这颗手榴弹是给自己准备的,遇到危险不能脱身时,拉响手榴弹同敌人同归于尽,不能当俘虏!也叫光荣弹。”
啊,“光荣弹!”原来由此得名。
168高地距166高地直线距离仅几十米,就在敌人占据的227高地的鼻子底下,完全在敌直瞄火力控制和炮火封锁范围之内。我们小心翼翼,翻过一个战壕的掩体,进入土石并存,石缝凌厉的一个石缝路,手脚并用,摸一步爬一步,慢慢地向前挪动。当时,只有一点月光,战场安静的有些瘆人,偶尔不远处传来一声鸟叫,让人毛骨悚然。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在砰砰直跳,连大气都不敢喘……
终于,在一个战士的带领下,我爬到一个很小的石头洞口,战士对我说:“这就是咱们的家”。我感到很惊讶,说:“这就是咱们的家?”。他马上摆摆手对我说:“别讲话,周围都是小鬼子,快钻洞!”我说:“不好钻呀”。他告诉我说:“腿先钻”。我刚把脚伸进洞口,里面就有人一下把我拉了下去,我咕咚一屁股坐在了一堆爆破筒上,洞里臭哄哄充满难闻的气味。
里边的2个战士抢着跟我握手、拥抱。班长王春文用861电台与连里联系,第一次听他在电台里讲话挺有意思,他说:“黄山,黄山,豆油顺利到达”。我不太理解,怎么管我叫“豆油”?王春文忙解释说:“排长,这是暗语。我们距敌人太近,敌人用的电台和我们型号一样,互相都能听见,许多越军都懂中国话,为了保密,我们在电台里要讲暗语。”
我们166、166无名等高地是在那拉口前沿的最底部,三面受敌。离敌人最近的哨位只有几米远,双方炮弹的误差,很容易落在这些阵地上,先前的连队每天在这里都有伤亡。这几个高地也都是我军打击敌人的出发阵地和火力配属的重要高地,犹如锋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心窝里,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虽然我们的身份是实习排长,但在阵地上其实就是战士。刚上阵地的我们心中十分紧张,特别是晚上站岗,总感觉有敌人要摸上来偷袭,总想呼唤炮火覆盖。
我和战士们轮流在阵地哨位上值班,眼睛瞪得圆圆的,像X射线反复扫描阵地的情况,连一草一木的变化都熟记心中。
大家常说的“猫耳洞”,就是在战壕底部再挖一个洞,洞是一米高左右的椭圆形,大一点的,里面由弓形波纹钢撑着,小的就是一个土坑,能藏人就行。洞的长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挖,在洞里有被子等卧具,可以作为休息时使用,人少时“猫耳洞”也可躺着。
而对我们阵地来说,“猫耳洞”可算是“天堂”。我们的“猫耳洞”是天然的石洞,坐着直不起腰,躺着伸不开腿。头上漏水,脚下踩泥,老鼠乱窜,毒蛇出没,蚊虫成群。
我们在前沿阵地哨位上与外面的联系主要靠861电台(全称是“861便携式指挥机”)。这种超短波小型电台采用了头戴式耳机与喉头话务器合二为一,从而解放了操作员的双手,耳机戴在头上,有个带子状的送话器,从脸颊系在下颚处,喉头送话器非常好用,使用声带振动的通话,如深夜耳语这样小声的条件下话音也很清晰。
我们的阵地离敌人很近,从来不敢大声讲话,在电台里通话只能靠“气声”。3个月后,当我们离开阵地到了安全地带,忍不住放声大喊,但没喊几声嗓子就哑了——声带已不能适应这样强度的发音了。
我们阵地前面是敌人的227高地,左侧是敌人的167高地,是前沿的咽喉要道,也是敌人火力封锁的重要目标,每天都要承受数以千计的各种枪炮弹。这座方圆不过百米的小山包,绿色植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白花花的碎石。
我们的石头洞里有3个战士,第一次看见他们,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班长王春文看上去岁数比较大,头发和胡子都特别长,前面看像大哥后面看像大嫂,他实际年龄比我还小。战士高峰身上长了许多疮,后来我在给他上药的时候数了一下,他全身上下共有96处,每个疮都有5分钱那么大,脓水顺着身体往下流。但他非常乐观,作战勇敢,从不叫苦。另外一个战士张玉生更有意思,他头上戴一个大钢盔,咣里咣当的,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泥了巴唧,除此之外,什么也没穿。后来,我们哨位又补充了一个新兵叫于世能,上战场之前他只打过5发子弹,还不会用班用轻机枪。刚上阵地时他很紧张,晚上站岗手里要拿着一根绳子与我连在一起,一会儿他就拉我一下,我也拉他一下。他觉得我在身边,心里就踏实了。
1985年9月5日,就在我们上阵地的第二天晚上,敌军突然向我们发起了进攻。炮弹一排排在哨位周围爆炸,刚刚平静的阵地,猛然间地动山摇,天崩地裂。巨大的爆炸声震得耳朵嗡嗡直响,硝烟涌进洞里,让人喘不过气来。
电台中传来排长王东山的声音:“敌人进攻了!守住阵地!”于是,我和战士们冒着炮火硝烟迅速冲出洞口。
突然,战士高峰猛地把我扑倒在地,几乎在同时,一发炮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一声巨响,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快被震出来了,气浪夹着石头粉末灌得我满嘴都是,味道苦苦的。高峰趴在我耳边大声说:“排长,你的姿式太高了!要注意防护。”还说了一句 “你是大学生,不能死啊!”
后来我了解到,在我们上阵地之前,连里通知过,要重点保护好这些大学生排长。在我刚上战场,还不知深浅的时刻,战士高峰的这一举动让我永远记在心里。我的好兄弟,你这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我啊!
我们端着枪扫射,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没过一会儿,敌人又一次向我们扑来。炮弹不断在我们周围爆炸,气浪把我头顶上的钢盔给冲掉了,对面敌军高地上的高射机枪子弹拖着红线交叉着从头上飞过,打在岩石上啪啪直响,火星四溅,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
我一看敌人来势凶猛,顾不上拾钢盔,急忙抱着半箱手榴弹跳到右侧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向敌投弹。接着又赶紧换了个位置,跳到另一个大石头后面。刚站住脚,敌人投来的一颗手雷在我刚才的位置爆炸,碎石落了我一身,我抱来的那个手榴弹箱子被炸飞了。王春文、高峰和张玉生趁机向敌人猛烈射击、投弹,友邻的2号、3号哨位也猛烈开火,敌人被打得退了下去。
这时阵地上的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照明弹腾空而起,周围一片白昼,爆炸的烟雾一团一团升起。
那天,我们的哨位打得还比较顺利,没有伤亡。但在我们旁边的2号哨位却有一位小战士牺牲了,他的名字叫张玉贵,刚在阵地上过完18岁生日。
当时,张玉贵与我军校同学丁文海同在一个哨位。当天晚上战斗打响后,丁文海正要冲出洞,张玉贵一把拉下他,说:“排长,你刚来,情况不熟,我先上”。但张玉贵刚一出洞口,一发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了,强大的冲击波把他和丁文海同时掀翻在地。丁文海顾不上自己身上的伤痛,爬起来一看,张玉贵头部和胸前都被炸开,浑身都是鲜血,眼睛睁得大大的。丁文海把他抱在怀里,使劲地喊着他的名字,只见张玉贵的嘴唇一张一张,想说什么,但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只觉得他的身体越来越沉、越来越凉……
这就是我来到前沿阵地第二天的战斗,第一次品味硝烟,第一次见证牺牲,以后我们的战场景况几乎天天如此。
1985年9月8日,敌人又一次向我们最前沿阵地发起反扑。战斗中,敌人的一颗手榴弹扔了过来,距战士李忠良和同学张元生只有半米远,在这危急关头,李忠良以迅猛的动作,用左手抓起手榴弹向洞外扔去,手榴弹出手就爆炸了,战友的生命和电台保住了,可李忠良却被炸断了左臂,鲜血喷射而出。当李忠良从昏迷中醒来,听到敌人的枪弹仍在呼啸时,他用剩下的一只手推开战友,说:“别管我,坚守哨位,消灭敌人要紧!”他扶着石壁,顽强地站了起来,双腿夹住手榴弹,用右手拧开盖,以顽强的毅力爬到哨位,用右手投弹,独臂架起冲锋枪射击。敌人被打退了,李忠良又一次昏倒在哨位上。
战斗结束后,李忠良被送到后方医院。战友们去医院看望他并祝贺他荣立一等功时,他的左小臂已被锯去,但他没有丝毫悲伤,仍然惦记着重返战场。他对部队范学政委说:“首长,我在战斗中已经实践过了,一只手完全可以打枪投弹,伤好后,我还要上我的战位,照样消灭敌人!”这话语撞击着人们的肺腑,在场的战友和医生护士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2015年,在一个战友儿子结婚的现场,我们又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三连战友。摸着李忠良生硬冰凉的假肢,我的心很疼。但李忠良却笑着说:“我很知足。我不跟活着的人比,比起牺牲的战友,我感到很幸运,很幸福了”。
战友李忠良英勇顽强,身残志坚,他血性阳刚的忠勇品格和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9月22日是我23岁生日,就在那天晚上,敌人又一次发动了进攻。战斗中,相距不足10米的战友张向东壮烈牺牲,战友刘广田和杨明政身负重伤。激战过后,我特别思念亲人。那天,我在给女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今天是我23周岁的生日,可能你和家里都记着这个日子,也许还要为我祝福一番吧!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是我最难忘的一个生日。隆隆的炮声今天格外响亮,象是为我祝贺,阵地上的战友虽然并未全见过面,但他们听说后,有的送来罐头,有的写来慰问信,打来“贺电”。最令人感动的是好几个素不相识的战士通过电台给我来了个“生日音乐会”,他们的歌虽然艺术性不够,但他们的心意却是无比纯真,是最优美的。他们还让我“点唱”节目,我第一个要的是《十五的月亮》,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想念远方的亲人,想念养育我的故乡,我也多么希望你能为我唱首歌啊!
说实话,在这里,每天都要用分秒计算时间,谁也不敢保证过一会儿没危险,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作了一切准备,我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幸运的,四次险情我安然无恙,使我能度过二十三岁的生日。就在昨天,敌军疯狂的一次炮击把我们的洞口炸塌了,我竟然能从乱石堆里钻出来,只是腿擦破点皮,真是“大难不死”啊!
我常想,人到底怎么样生活才有意义?看到我们在这里吃苦受罪,流血牺牲,可能会有一些人认为是“吃亏”。是的,我们的确失去了许多常人应该享受的欢乐和幸福,但我们同时也得到了常人所得不到的自豪和光荣。不是吗?有谁能骄傲的说,我的身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谁能把二十几岁的生命和十亿人民的幸福紧紧相连?有谁能让自己的青春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燃烧?又有谁能在这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奉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
是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军人!9月16日凌晨5时许,我正在洞口值班,3个敌军趁着天黑偷偷地摸了上来,待我发现时,最近的一个离我只有三、四米远了,我来不及报告,便立即将早已握在手中的手榴弹扔了过去,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在逃跑中,甩过来一颗手雷,在我左侧两米左右的石坎下爆炸了,一块弹片“铛”的一声打进我的钢盔,正好卡在护圈上,我的头发被烫黄了一小片。看见敌人被炸倒,我心里快乐极了。
告诉你,我刚来不久,一个小战士刚刚过完他二十岁的生日,就在敌军的一次进攻中,永远地倒下了。二十岁,这是多么神圣的岁数!在这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刻,他却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只把一道光亮留给人间。
今天过生日,在接受战友们的祝贺时,我同时也想过牺牲,也许我也会和那位小战士一样,刚过完生日不久,就被炮弹炸飞,被子弹射穿,但能把血流在这阵地上,把生命献给保卫祖国的战场,我不感到遗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我人生的信条。
请你原谅我毫不隐瞒地跟你说这些,如果我真的“光荣”了,我的战友会送你阵地上一块石头,石头虽然被炸碎了,但永远是石头。人也应该是这样,不论生还是死,都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个有意义、有作为的人,你说是吧?
按照当时的规定,军校来的见习排长在前沿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0天,但我们这批学员在阵地上坚守了77个日日夜夜,与战友们一起打退了敌人上百次进攻和偷袭。
在战斗的间隙,为了鼓足士气,我们在阵地上开展了“读家信,写家信”活动。
在战斗最激烈最艰苦的时刻,我收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这封信很快在前线阵地上传开,给我和战友们增添了战斗的力量。我下阵地后这封战地家信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2022年6月,在喜迎党的二十大之际,恰逢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馆藏原创策划的“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在国博北8展厅向公众展出。展览从家国情怀这一角度,鉴选馆藏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家热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等珍贵文献以及各类实物170余件。妈妈的信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单元展出。
文物简介中这样写道:胡国桥,1984年7月入伍,1985年参加云南老山防御作战,荣立一等战功。胡国桥母亲写信鼓励他英勇杀敌为国争光:“代(带)着全家人的希望与嘱托入了军校,上了前线,接受那血与火的烤(考)验——灵敏度最高的试金石。在这一点上,全家人是放心的。我可以大胆地说,我的儿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出光和热的,都会做一名祖国和我们骄傲的儿子!”
相比展览中李大钊、何叔衡等革命先辈的珍贵手稿和文物,这封信写于新的历史时期,年代虽然没有那么久远,但它包含了同样的使命担当。
在当时的战场上,我先后八处负伤,伤口感染严重溃烂,高烧不退,多次昏迷,上级多次要我下阵地。但是,我觉得在阵地哨位上我的职级最高、年龄最大、文凭最高,战士们都信赖我,我一定要与他们共同战斗到最后。
我用指甲抠出化脓伤口中的弹片,坚持不撤下去。直至1985年11月19日,部队换防我与战友们最后一批撤下阵地。此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因伤口感染已得了严重的败血症。我被伤员专机紧急送往昆明医院抢救,幸运地从死亡边缘上闯了过来。至今,胸口下面的一块弹片已与骨头永远长在了一起。
战后,我所在的连队被授予老山“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我本人荣立了一等战功。我感觉到,虽然军功章佩戴在我的胸前,但是,里面却流淌着无数英烈的鲜血,凝聚着所有前线战友的荣耀,绽放着共和国战士的光辉。
我们胜利了,凯旋了。军区首长为我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后来还为我的孩子取了名字:“丹”(意为一片丹心报祖国)。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对所有参战军人的鼓励和褒奖,也是对我们保持荣誉、传承红色基因、再立新功的殷切期望。
从战场归来后,我默默收起了军功章。瞄准未来高技术条件局部战争的需求,开始了人生新的冲锋,决心为打赢下一场战争再立新功。
多年来,我坚持在部队基层工作。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曾先后4次主动申请免职入校学习、转岗,完成了一次次人生跨越。1997年我35岁,时任副大队长,以北京军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陆军指挥学院作战指挥专业,攻读军事学硕士研究生学位,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2005年,我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任军事模拟中心主任,创建了全军初级陆军学院第一个作战实验室,但当得知陆军航空兵在扩大发展需要人才支援时,毅然辞去主任职务来到陆航,成为一名普通科研人员;2009年,原总参陆航部准备把我正式选调到机关任职,但我认为保留技术级可以多在部队服务几年,搞科研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就谢绝了领导和机关的好意,写申请回到了科研工作单位。也许有人觉得搞科研没有显赫的职位和令人羡慕的权力,但我认为科研干部同样心中有理想,肩上有使命,人生有追求,工作有意义。
2011年,我承担了“陆军航空兵战术研究”课题,该课题任务书面成果形式的要求原本是“研究报告”,但我带领课题组主动扩大研究范围,增加研究内容。期间,为深入研究高原直升机作战使用需求和战法运用,我不顾强烈的高原反应,带着氧气瓶,冒着山体滑坡、泥石流和道路塌方的危险,走遍了川藏线的每一个直升机起降点和中印边境的最偏远边防连队,最终形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并作为训练参考类教材向全军陆航部队发行。
协同是信息化条件下陆航参加联合作战和融入陆军的重要问题,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为此,我长期坚持对联合作战陆航协同理论、协同技术、协同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十年磨一剑”,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我最终拿出了19个专题研究报告和4部专著。2014年,这个项目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实现了陆航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奖的新突破。
多年来,我紧紧围绕“陆军航空兵建设发展重大问题研究”系列课题,深化兵种军事理论创新,追踪陆军航空兵战略和作战运用等重大问题,先后主持完成几十项重点科研项目,有效解决了兵种建设发展理论支撑不足、作战基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陆航空突部队在典型作战运用方法欠缺和缺少实战经验借鉴等重难点问题。2022年,“陆军航空兵建设发展重大问题研究”项目荣获全军军事理论成果二等奖,上级领导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2023年11月,我作为“陆军航空兵建设发展重大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参加了陆军重点军事理论成果展。
入伍40年来,我始终把为军队建设多做贡献当作自己最高的人生追求。
由于当年战场负伤和高度紧张的“猫耳洞”战斗,以及烂裆等疾病,使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皮肤过敏等战争后遗症。多年以来,我晚上无法睡得踏实,稍有动静就会惊醒,常常在梦中猛然坐起来,甚至拳打脚踢。阴天下雨胸骨处的伤口总是隐隐作痛。而腰部经常出现的一片片红肿,奇痒无比,更是让我难以忍受。为了克服头痛、腰痛,我常常用毛巾沾上冷水系在头上,用热水杯子顶着腰坚持工作。有时腰疼得实在受不了,就躺在床上写;头晕眼花看不了电脑,就让其他同志甚至发动爱人和女儿帮助念稿子、配合修改材料。多年来,上下班对我来说只是工作地点的转移,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已是经常的事。
2022年,我已到达最高服役年龄,即将退休。但我坚决要求参加陆空联合军事演练,在内蒙古朱日和大漠草原连续奋战3个多月。演习期间,有一颗牙齿突然开裂,剧痛难忍,领导和同志们都劝我赶紧回北京医院看看,但我执意去部队卫生队让战士拔掉伤牙,咬着纱布继续坚持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陆军机关通报表扬。
多年来,我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先后主持完成了几十项军队重点课题研究任务,对陆航发展、作战运用、装备建设和综合保障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出版了《陆航建设发展理论研究》等一系列著作。获全军“十五”“十一五”军事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3项,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9项,获全军军事理论研讨会优秀成果一等奖7项,公开发表学术文章150多篇,为陆航兵种建设发展和作战运用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推进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我积极响应习主席“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号召,承担了大量坚定理想信念、培育战斗精神、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教育工作。在授课中充分结合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和实践体会,注重用强军报国的真情感染人、用鲜活真实的事例打动人,收到了良好教育效果。
近年来,我还主动申报并承担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老山精神研究》。多次赴边境战场旧址和当年作战部队调研,走访当年参战老兵,收集整理了大量文字、视频资料和图片,多次去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等地祭奠牺牲战友,资助了多位生活有困难的参战老兵和烈士家属,参加了全国“英模进校园巡讲”活动,发表了400多篇弘扬我军战斗精神等相关文章,主编出版了记述老山英雄事迹的《血染的风采》《血染的答卷》等著作。
适应信息网络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针对网上出现的诋毁抹黑英雄的现象,我让妻子创办了“英雄旗帜”微信公众号,撰写发表了许多讲述英雄事迹、弘扬我军光荣传统的文章和视频短片。多篇文章被多家官方网络媒体刊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多次被评为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和正能量榜样。
近些年来,不少人只看到金钱的作用,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扭曲。在有的人眼里,那些为国家利益牺牲的革命烈士不再是崇拜的对象,而把歌星、影星和腰缠万贯的富豪当做膜拜目标。所以,我积极倡议,当前不仅要反复论述英雄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性,而且还应唱响新时期英雄的赞歌,让英雄的名字真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响起来,让英雄的形象在青少年的心中树立起来。
2015年初,我被确定代表本单位参加优秀“四会”政治教员评比,在机关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克服年龄大、工作多等诸多困难,深入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精心准备授课文稿和多媒体课件,先后两次参加了陆航部和总参组织的优秀“四会”政治教员综合评比活动,均获得理论知识考试、基本能力测试、课堂现场授课和情况问题处置四项考核总分第一名的突出成绩,受到总参谋部通报表彰。同年11月,经总参和总政综合考核,我被评为全军优秀“四会”政治教员。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每当这首《英雄赞歌》的旋律响起,我都会心潮澎湃。我从小就崇拜英雄,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等等,都是我的偶像,每一次看电影《英雄儿女》,我都会热泪盈眶。
如今,我已光荣退休。想起当年大学毕业后一同参军入伍的同学、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重残了,比起他们,我既感到幸运,更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告诫自己,要永远发扬光荣的老山精神,当好我军战斗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为打赢下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本文原载于《人民文学》2023年增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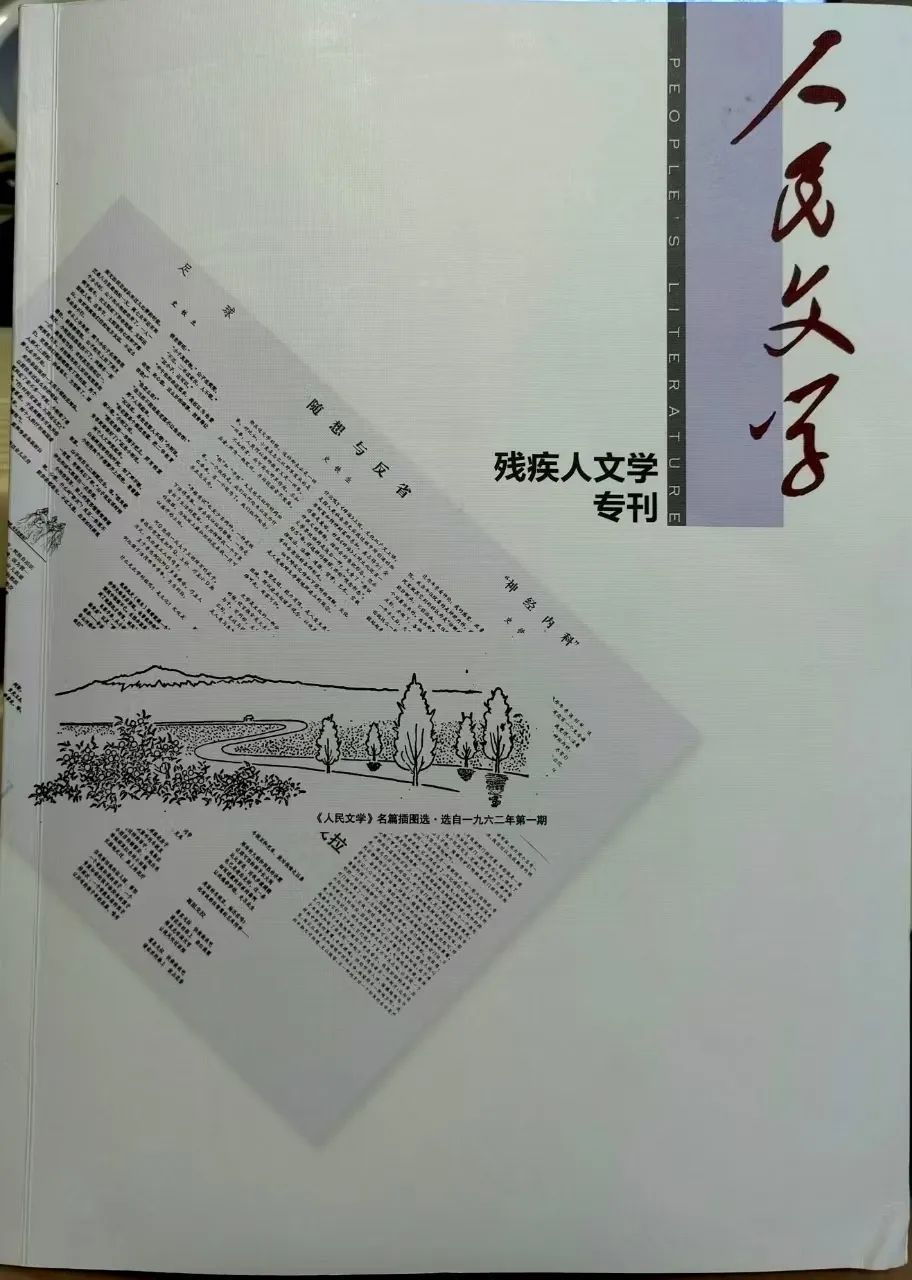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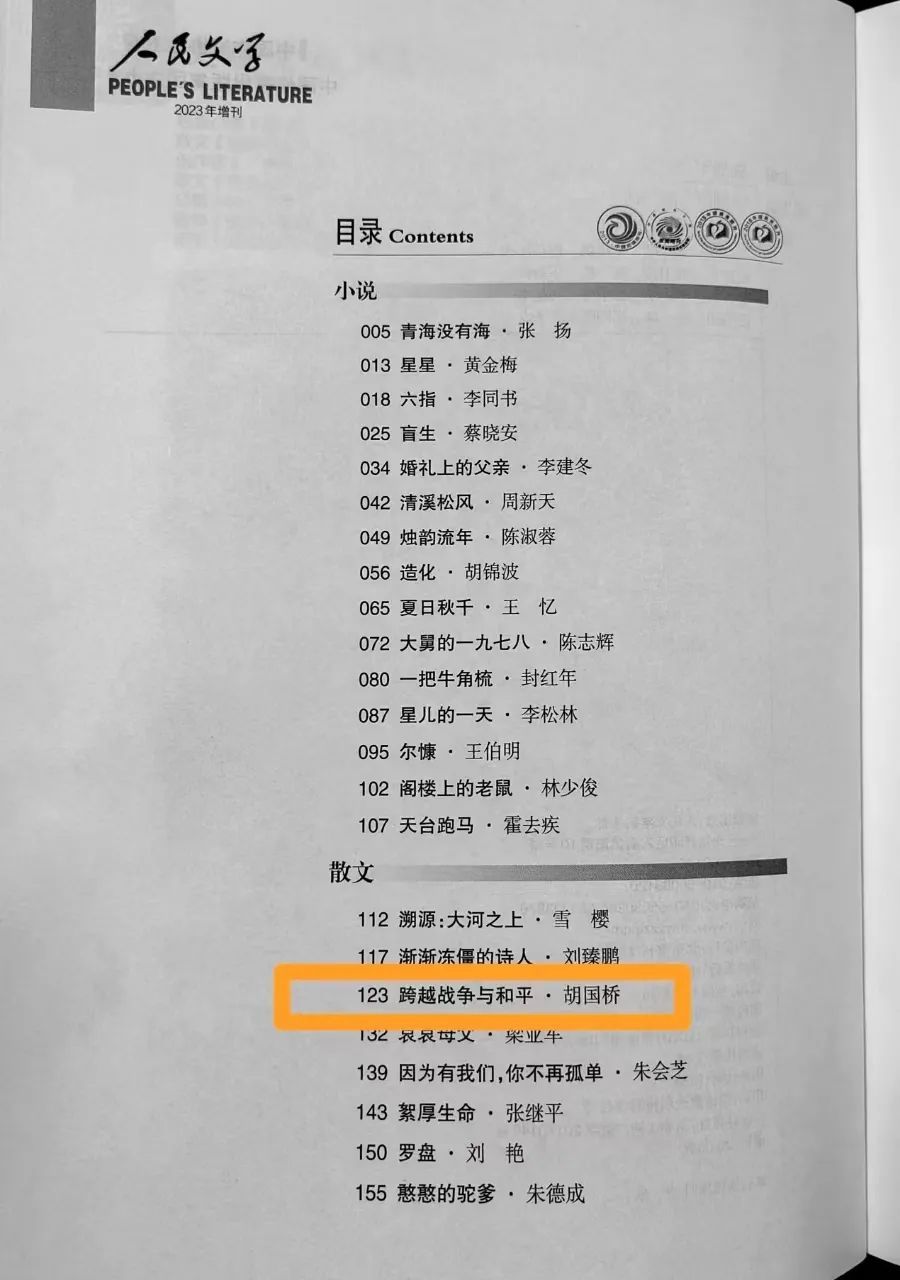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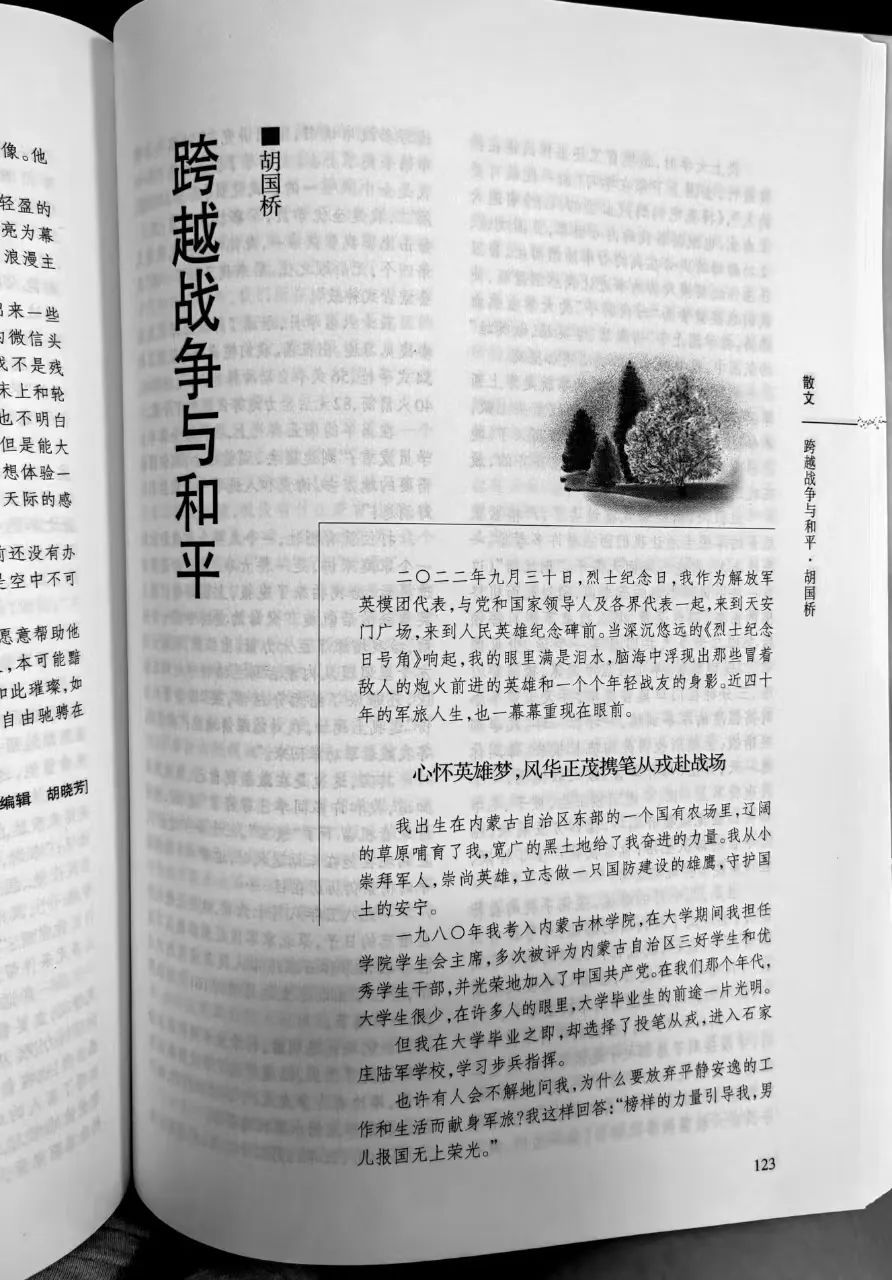
来源:《人民文学》
编辑:刘思奇
初审:王瑞霞
复审:杨逸隆
终审:郭松朋



